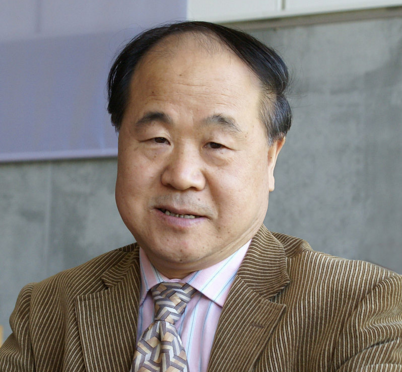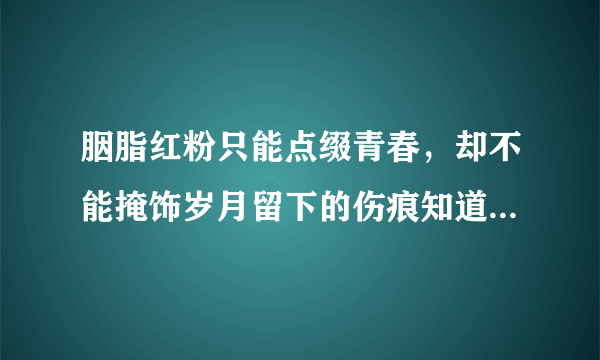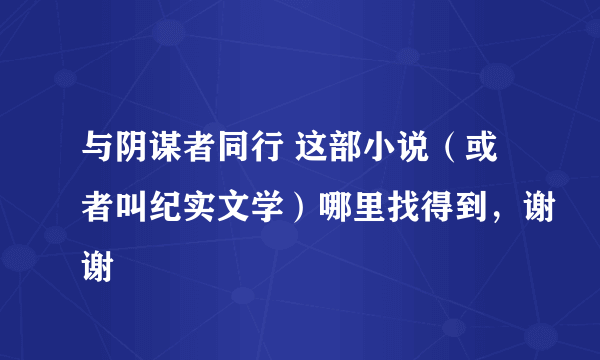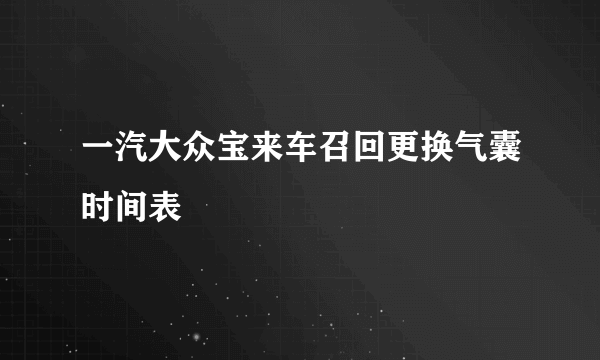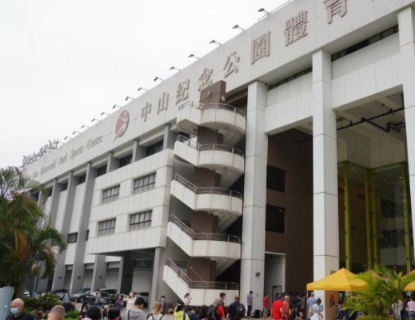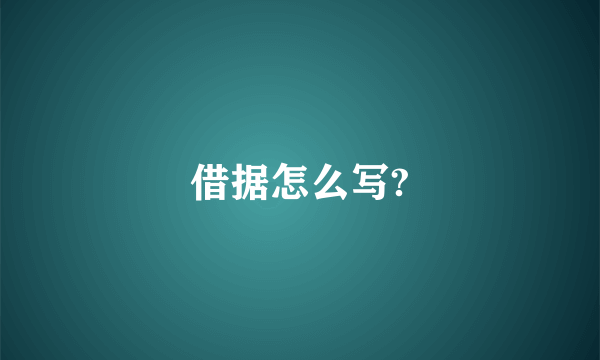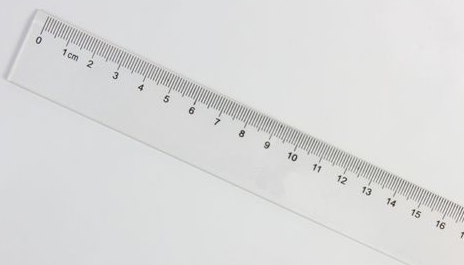中国的“伤痕文学”和苏联的“解冻文学”的区别是什么
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: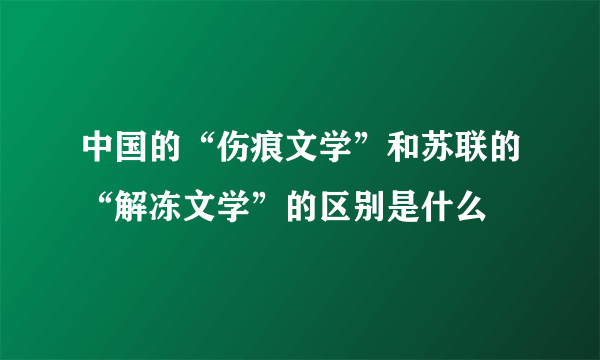
前苏联的“解冻文学”与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兴起的“伤痕文学”有着相似的兴起背景、文学内涵;但“伤痕文学”更感性化,更偏向于抒发人的伤痛和愤怒之情;“解冻文学”由于苏联国内外环境的压力最终消散了,“伤痕文学则随着中国思想解放的进一步展开和改革开放的进行,进一步发展并且深入下去。 前苏联的解冻文学出现于上世纪的50年代,中国的解冻文学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末。尽管时间上相隔20年,二者之间在出现背景、文学内涵等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,但他们的走向与命运却完全不同,这些是值得我们思索的。 前苏联的解冻文学与中国的伤痕文学出现的背景是相似的,这源于中俄二国国情尤其是体制方面在一段时期内的相似,或者说,源于中国对苏联体制的模仿。由于斯大林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僵化、专制化,斯大林时代的文坛大都是歌颂文学,宣扬“无冲突论”,造成了文学的公式化、概念化,文学作品回避矛盾、粉饰生活、歌功颂德,对于一些稍微触及现实的作品,动辄加以粗暴的攻击、批判。斯大林逝世后,苏联第二次作代会召开,彻底纠正“左”的偏向,作家们开始大胆表现生活矛盾的冲突和社会的黑暗面,“解冻文学”由此出现。中国的“伤痕文学”出现背景与此有着异曲同工的背景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作为新时期文学的第一股巨大浪潮,“伤痕文学”一反“文革”时期“高、大、全”式的呆板、僵化、空洞的创作模式,主张立足于现实生活,以批判的眼光回顾历史,暴露了十年“文革”造成的严重灾难及其在人民灵魂深处留下的难以消弥的创伤。可以说,二者出现的背景是极其相似的,僵化的国家政治生活的变动直接促使了文学的变化,激起了文学的生命力。 “解冻文学”和“伤痕文学”在内涵方面基本也是相同的。“解冻文学”以爱伦堡的《解冻》为发端,开创了一个文学潮流。首先,二者都要求重视人,呼唤人性的复归,要求重新确认“人”的地位,要求文学站在“人性本位”的高度,直面和批判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弊端。解冻文学之前的苏联文学作品往往写事重于写人,“生产小说”、“商业小说”、“农业题材”、“工业题材”等都是指写事,而不是写人,解冻文学力图走出这种文学误区。伤痕文学之前的中国文学也是忽视人,践踏人权,尤其是文革对人的肆意践踏,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,卢新华1978年8月发表于《文汇报》的短篇小说《伤痕》及其有关引发的“暴露”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,人们开始思索历史,思索人在历史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;其次,要求重新发掘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,打碎即往的虚伪的、矫饰的既“瞒”又“骗”的政治口号式的创作毒流。1953年底至1954年上半年,苏联的《新世界》导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,它们触及到了当时十分敏锐的社会问题。其中,波麦兰采夫的《论文学的真诚》最有代表性。该文揭露了文学中“粉饰现实”的种种积习和手法,呼吁作家拿出“真诚”和“良心”,写“生活的真实”。这一问题的提出,立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,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。苏联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一连串反官僚主义题材的小说,如亚·雅申的《杠杆》、丹·格拉宁的《个人意见》等。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些在30年代遭镇压而死的作家的作品。 当然,“解冻文学为”与“伤痕文学”的不同之处还是存在的,“解冻文学”倾向于对过去的僵化的文学模式的反叛,更多的是以一种理性的、清醒的态度来对待历史,对待现实生活。而“伤痕文学”则环绕着一种沉重的悲剧气氛,重泄义愤,轻理智认识。在许多伤痕文学作品中,我们不无震撼地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沉重,伤痛而愤怒的情感流淌其中,处处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情感冲击力。可以说, 解冻文学更重理性,而伤痕文学偏重感性。 中俄的这二种文学潮流最大的区别还在于走向与命运的不同。苏共20大后,思想解放界的“解冻”思潮一泻千里,波匈事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边串事件接二连三发生,加上国内出现“莫斯科大学事件”,使苏共领导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。从1957年开始,便开始收紧“解冻”的闸门,特别是对文艺界的“不健康倾向”的批判,随后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,“解冻”思潮便基本停止发展。在1959—1960年期间,“解冻”的闸门虽没有关死,正常的平反虽还照常进行,但思想解放的步伐却大大放慢了下来。 中国的“伤痕文学”则由于思想解放的开展和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,而且,继“伤痕文学”之后,“反思文学”、“寻根文学”等进一步兴起,对于历史的追问,对于现实的思索,对于未来的探求,也更进了一步。 综上所述,“解冻文学”与伤痕文学虽然在发生背景与文学内涵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,但所取的对历史和现实生活和态度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,其走向更是差别巨大,发人深省。